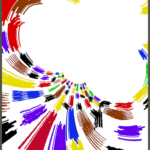我曾問過木頭人黃檜木,在他五千年歲月裡,有沒有什麼令他印象深刻的人、事、物呢。
他告訴我,他也有好幾個印象深刻的人,其中之一,便是拿破崙(Napoléon)。
我原本以為他會說的是老子、莊子、項羽或是達文西……等古代哲人或英豪,但沒想到他提到的是那位法蘭西的名人。
「為什麼?」我追問。
「因為他以驚人的意志攀上權力巔峰,又因無盡的雄心而從頂點跌落的人類史詩,以最後的平靜接受命運的落幕。他曾有過一段不凡的故事,一個關於最終選擇順從,而非強行征服一生的故事。」木頭人說道。
接著,木頭人那雙紋理清晰的手輕輕一揮,開始向我描訴,他與拿破崙在聖赫勒拿島(St. Helena)相處時,拿破崙告訴他的故事。
***
那年是西元1819年。當時的我正旅居歐洲,我的奇特事蹟早已在貴族與知識階層中傳開。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八剛從拿破崙手中奪回政權,出於一種複雜的心理。或許是勝利者的嘲弄,或許是想為大西洋孤島上的前皇帝添加一點戲劇性的慰藉,竟決定聘請我這位來自東方、有生命力的木頭人,前往聖赫勒拿島進行一場特別的會面。
我對此興致盎然,一口答應。我對拿破崙的興趣,不只在於戰場上那雷霆萬鈞的軍事指揮,更因他為歐洲立下的《拿破崙法典》,那部為現代文明奠定基礎的理性骨架。
當我踏上那座遙遠的火山島時,海風鹹濕,濃重的霧氣像舊夢般纏繞在嶙峋的峭壁之間,久不散去。
拿破崙坐在他莊園陽台的茶几旁,仍披著他穿習慣的那款深藍色軍袍,眼神深陷,凝視著灰暗的海線。他眼中已不見昔日征戰時的烈陽,只剩聖赫勒拿的霧氣。
當他初見我這個會說話、會走動的木頭人時,沒有一絲驚慌失措,反倒微微一笑,那神情竟有些孩童般的純真。
「你是上帝創造的嗎?那你算是植物?還是人類呢?」拿破崙說道。語氣平靜得像在評論天氣。
「我是由不同的上帝所創造的。祂要造的,主要還是人類,只是不小心,用錯了材料吧……」我回應。
拿破崙聽完後,便不拘小節地請我坐上茶几。我聞到旁邊那杯濃烈的咖啡香,感到島上輕風吹拂的陽光也顯得柔和了不少。
「你……是如何誕生的?」拿破崙問道。這是他第一個問題,但在接下來幾天的談話中,他習慣不時地打斷我的回答,追問更多的細節,如同戰場上追蹤敵情般精準。
我除了說到女媧造我的古老傳說,還說了我在五千年歲月裡,經歷不同事件的人間興亡、帝國起落。我翻開了手腕上的年輪,那如時光之書的橫截面,向拿破崙展示了幾千年前的氣候特徵,或是曾被古人刻下的歷史圖騰。拿破崙聽得津津有味,彷彿暫時忘記了自己的流放與失敗。他像回到了少年時代,那個熱愛閱讀和浪漫幻想的科西嘉島年輕人。
一直持續到數天之後。那天午後,暴雨驟起。
那是南大西洋典型的驟雨,風勢猛烈,彷彿要將整座島嶼連根拔起。拿破崙起身去關窗。當他轉身時,臉上的表情已不再是那個沉醉於奇幻故事的聽眾。
「我想讓你聽一個秘密。世人不會懂的。是關於一根手杖的傳說。」拿破崙的語氣低沉,充滿了過去的重量。
他那雙鷹眼望著我,彷彿要穿透我層層木製的軀殼,直視我五千年來的靈魂。他終於向我說起,他最隱密的一段往事。當時拿破崙口氣裡帶著一種被壓抑已久的驕傲和痛楚。
***
那一年是1798年,我突然遠征埃及,不是為了那幾座金字塔,也不是為了應許之地。因為我搜尋許久的目標,終於找到了。那就是摩西當年使用的手杖。我則稱它為應許之杖。
我帶著自己的學者與軍隊,穿過金字塔的影子,翻越西奈半島的岩谷。來到西奈山脈的那片土地,周圍盡是毫無生命的山脈。太陽的軌跡,在日出與日落間變動,光線角度所譜出的色彩,繽彿如同神的注視。
那地方太空了,連雲都不敢經過。我在那裡,看見比戰場更深的寂寞。
我心中的計劃是,一旦獲得這根應許之杖,我倒不是要降下十災。而是需要像摩西分開紅海一樣,分開法蘭西與英格蘭之間距離最短的多佛海峽。法蘭西強大的陸軍將直接踏上英國本土,徹底擊潰宿敵。這是唯一能彌補法蘭西海軍劣勢的神之策略。
後來,我的搜查團隊終於找到線索。在一處摩西後裔的隱居地,把那根應許之杖從一個古老的木匣中取出。
然而,當我親眼見到它時,我的心卻微微一震。那不是神器,而只是根平凡的原木手杖,樸素得像鄉間老農的長拐杖。我試著握在手裡,卻沒有感受到任何神蹟的氣息。
那時,摩西的後裔,一位滿身鞭痕卻仍昂首的長者,被押解至我的面前。長者沒有恐懼,只有一種對天命的悲憫。
「不要使用它。那是試煉,不是武器。你的臣民會因它而受罰,流浪、被欺凌。這杖屬於天道,不屬於王權。」那老者以微弱的聲音對我說道。
「為什麼!力量就是力量,勝利不就是正義嗎!」我當時回道。
「因為宇宙是守恆的,將軍。你們稱之為物理,我們稱之為古老的代價償還。所有的奇蹟,代價都會由與施法者同族、同地的人來支付。」
「我們的祖先只是用它來逃離統治,就用四十年在西奈流浪的痛苦來償還。而你,如果用此杖去破壞發動戰爭、破壞自然法則,我相信你的族人所要付出的代價,會讓他們得到可怕的應許……那將會是流血、奴役與更大的代價。」摩西的後裔看著我,眼神中充滿了堅定的回答。
我的手緊緊握住那根木杖。腦海中浮現出分開多佛海峽的壯闊景象,這是可以徹底征服英格蘭,成為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救世主的機會。
「你是在製造恐懼!你在試圖保護你的神話嗎!」我望向摩西的後裔,憤怒地質問。
「我保護的是定律!你雖然像風暴一樣席捲歐洲大陸,但相對於世界,你是無法對抗這整個世界。更何況相對於天神。你現在的成功,是軍事天賦與時代順從的結果。如果你試圖強行改變天道,你將會被更巨大的反作用力吞噬。我們只希望,你能順從這個定律,選擇一條令世人較少痛苦的道路。」摩西後裔說。
我無法立刻做決定。那幾天,我將手杖隨身帶著,待在西奈半島的聖凱瑟琳修道院。我反覆觀看那根樸素的木杖,感受它所蘊藏的歷史重量。我意識到,這根杖彷彿是用來檢驗人心的。
數天後的黃昏,一場極度乾燥的熱浪來襲。軍隊陷入混亂,水源耗盡。我突然感到,這是否為應許之杖的試煉時刻?如果用它來立刻召喚水源,那摩西後裔的警告會不會只是空話。
我舉起了木杖,雙目緊閉。在烈日的熱浪中,似乎感受到了泉水的湧出,也同時聽見了軍隊的歡呼,以及未來戰場上無數亡魂的低語。又彷彿看見摩西後裔用那悲憫的眼神看著我,以及他身後那片無垠的、毫無生機的西奈山。
我猛地睜開眼睛。我雖然是西方理性的信徒,但那種東方宿命論的警告,卻如冰冷的鐵釘般釘在我的心頭。
最終,我沒有在埃及使用應許之杖。也因當時的法蘭西國內的局勢,已不容許我再長期滯留埃及。時機未到,我決定先保留這力量,讓它有機會再為我的帝國服務。我將那根樸素的木杖,藏入隨身的箱籠中,沒有對任何人透露它的秘密,除了幾個親近的心腹。
我當時順從了個人膨脹的野心,而非世上的道德法則。我相信,這根杖只是在等待一個,更「值得」犧牲部分人民來換取最終勝利的時刻。
法蘭西帝國已達到權力的頂峰,卻陷入了與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長期僵持。最後為了迫使沙皇屈服,我集結了六十萬人馬,前往俄羅斯的首都莫斯科。
時間來到1812年9月,征途初期一切順利得令人不安。直到那年秋末,俄羅斯人撤退時使用的焦土政策,加上莫斯科的冬季漸漸來臨,將大軍團拖入泥沼。補給線斷裂,非戰鬥所傷導致兵力不斷下降。
於是我決定先行徹出俄羅斯,直至最後在退出俄羅斯,即將回到東歐的途中,俄軍仍一路纏鬥追擊。最後我軍在別列津納河(Berezina River)遭遇了最可怕的困境。俄軍從兩側包抄,而眼前本是該被冰雪冰封的河流,但不知俄羅斯人用什麼方法,竟然讓河冰破裂成不易度河的狀態,軍隊人數眾多,如強行通過,河面隨時可能崩塌的。這是軍事常規力量無法解決的死局。
1812年10月下旬,在別列津納河畔,我再次感到了來自天意的嘲弄。當時我下令工程師搭建浮橋,但那根本是徒勞。我的士兵們被冰凍、被追擊、被絕望吞噬。
就在病倒的人愈來愈多,整個軍隊已被拖累到無戰鬥能力時,我拿出了最後的底牌「應許之杖」。我握著那根樸素的木杖,站在河岸邊,寒風呼嘯。我心中對安然度過的極度渴望,終於壓倒了摩西後裔的警告。
『這不是為了征服英格蘭,這只是為了拯救我們的軍隊,拯救我們的帝國。』我對自己低語默默的這樣告訴自己。
我閉上眼睛,將所有心力灌注到杖中。
神蹟發生了。
那根杖並非分開河流,而是讓別列津納河的水面結成厚實、堅硬,足以讓數萬人快速通過的冰層。這不僅是奇蹟,更是對自然法則的巨大扭曲與借貸。法軍得以在俄軍圍攻前,迅速通過了這條死亡之河。
應許之杖的力量為我獲得了這場戰役成功的撤退。
然而,守恆定律並未缺席,它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
應許之杖從自然界強行借貸來的巨大「寒冷」能量,在法軍過河之後,則以因果報應的方式,即刻反作用到現實世界。
極端的寒冷,讓撤退中的法軍面臨無法解釋的生命力枯竭。補給品的不足,士兵的意志力與體力,彷彿被那根杖瞬間抽取一空。撤退的過程變成了一場無法解釋的生命力崩潰。俄軍也因極端寒冷而傷亡慘重。我們這場戰役不是被對方擊敗,而是彼此都被無形的力量擊潰。
在離開俄羅斯邊境後,人數從起初的六十萬大軍,最終只剩不到四萬人。這數十萬的生命,不只是戰死,更多的是因寒冷、病痛而將生命力耗盡。我後來經過許久才知道,俄羅斯的傷亡人數也達到四十萬人。
原來應許之杖對強行改變命運所付出的代價,是如此巨大……。
***
在聖赫勒拿島,拿破崙的莊園客廳裡,寂靜時,只有壁爐中火焰些微的燃燒聲響。
「我以為我能操控它,或者說能用勝利來彌補一切。但我沒有。自那次使用之後,我再也沒有使用過那根木杖。它成了一個不斷提醒,法則不可違逆的詛咒。
後來一連串的戰事全都以失敗告終,甚至滑鐵盧之役。我連續的戰敗,用我的帝國,支付了應許之杖那瞬間的神蹟。我都不是敗給了敵軍,而是敗給了那根木杖所代表的守恆定律。
我這一生,都在領導,都在命令。但我最後的覺悟,是學會了對法則的順從。只是代價太高昂。」拿破崙說道。
「您曾在最高權力面前,體會了那只是相對而言的權力,並且最終選擇了對宇宙法則的順從。您征服的不是世界,而是您自己的傲慢。
我想……那根木杖不是給英雄的,而是給願意順天的人。」我對著這位前皇帝說道。
說完後,我默默地看著他,看著這位曾經撼動歐洲大陸的巨人,在聖赫勒拿這座孤島上,分享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戰役。
拿破崙深邃的眼神望向窗外,彷彿穿透了那片灰暗的玻璃窗。
「你,不老不朽,看盡了世界的全部。而我,只活了五十歲,卻看透了法則的無情。我們都是被命運選中的孤獨者。」他停頓了一下,眼中閃過一絲解脫。
「或許,我的流放,就是對我試圖逆天而行後,最後的隨遇而安吧。」說完後,拿破崙沒有任何豪言壯語。他伸出手,輕輕拍了拍他披著軍袍的雙腿,發出兩聲沉悶的擊打聲,然後站了起來。
他再度走向窗戶,沒有回頭,不知是看著窗外逐漸停歇的雨景,還是玻璃上倒映著官邸客廳的微光。風與浪的聲音與從遠處傳來,像是一首無盡的輓歌。
隨:元亨。利貞。无咎。
初九:官有渝,貞吉。出門交有功。
六二:系小子,失丈夫。
六三:系丈夫,失小子。隨,有求得利,居貞。
九四:隨有獲,貞凶。有孚在道,以明,何咎。九五:孚于嘉,吉。
上六:拘系之,乃從維之。王用亨于西山。